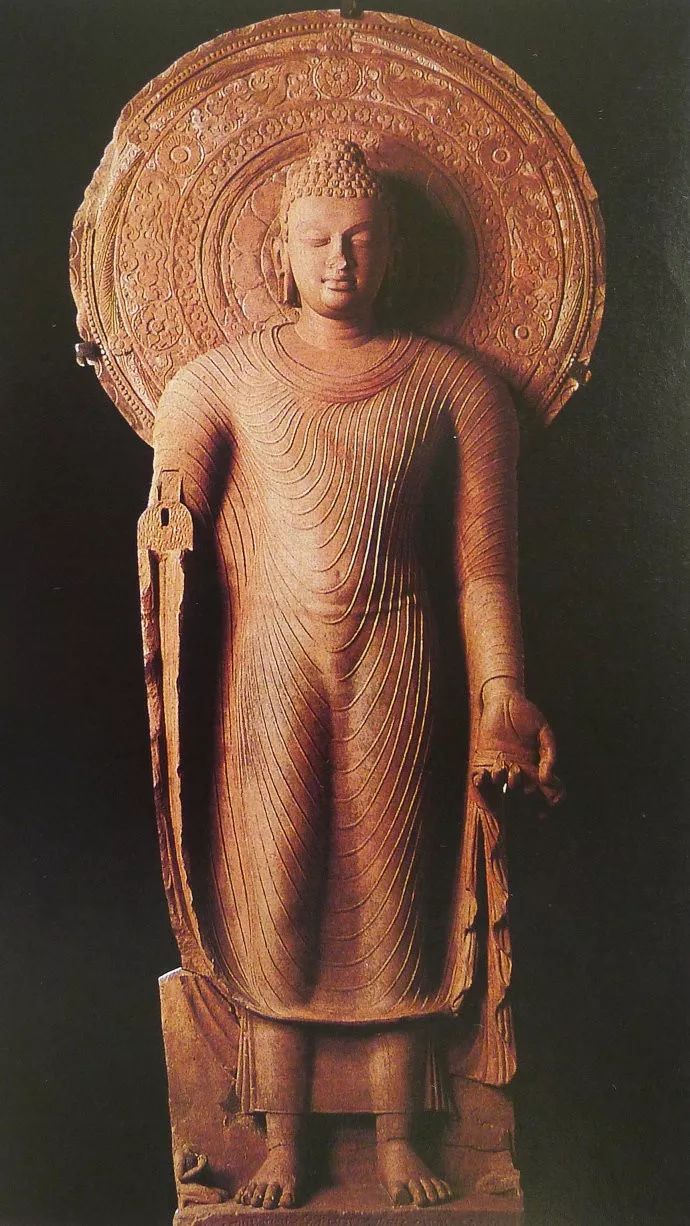
目录
“出离心”是解脱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。修行者在没有成就阿罗汉前都是要具备有出离心的。讨论出离心会帮助我们真正认识解脱道。认识出离心,成就出离心,能很好地帮助我们成就解脱。“出离心”的修法在藏传佛教里比较受重视。当代的南传佛教就是解脱道,它不需要特别去强调这个概念。汉传佛教传统的宗派重菩萨道,不太重点谈出离心,现在的根机也不如古人,所以在当代中国大乘佛教的背景下,应该注意“出离心”及其修法。
一、出离心的界定
什么是出离心?认识到三界是苦,希求解脱轮回的心,即是出离心。像佛经里面说的“三界火宅”,我们能感觉到三界没有安逸舒适的地方,就像生活在着火的房子里一样痛苦煎熬,要尽早出离。在宗喀巴大师的《三主要道》里,他对出离心有一个界定:“于诸轮回诸盛事,刹那不生羡慕心,日夜欲求得解脱,尔时已生出离心。”就是说,我们对世间的名、财等都没有希求之心,没有欲求心,不去追求它,时时刻刻想要出离,这就是出离心。当然,其实我们是很难做到日日夜夜、时时刻刻都要出离,但是宽泛地说,我们厌离轮回,希求得解脱,这个心就是出离心。
二、中印文化的差别——重世俗与重出离
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,可两个古老的文明有所差别。印度传统文化重宗教,重出离,而中国儒道文化重世俗。
(一)儒家、道家文化
儒家提倡的是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这是它的主旨,所强调的是入世。像《大学》里说:“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道家文化里有“羽化成仙”,从佛教来看,“成仙”最多也就是达到天界。所以还是在三界里边,在世俗里边。所以,中国文化中的儒、道文化还是偏重世俗的。
儒家和道家思想里面有没有出世的成分呢?也是有的。比如儒家也说: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,也有出世的内容。道家说“与道合一”,当你与道合一的时候,也没有世间的杂染在里边。虽然说道家也有出世的成分,但比如说他们求成仙,还是在世俗里边。所以大体上来说,儒家和道家还是偏向世间的,比较重世俗的。
(二)印度文化
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不同,它是比较重出离世间的。佛陀在世的时候,印度的宗教非常发达,有九十六种外道。现在的印度,宗教也是比较发达的。比较早期的典籍,如《奥义书》里,就说了解脱的内容。像其中较早的《广林奥义书》4,4,8中说:“智者,即梵的认识者,在身体衰亡后,直升天界,达到解脱。”也就是说,印度宗教也是讲出离轮回、讲解脱的,只是在见地上和佛教不同。他们认为,由“梵我合一”而达到解脱,只是佛教并不认同这是最终的解脱。他们只是在某种境界里,在某种天界,或成为梵天,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,其实都是没有达到最终的解脱,没有出离三界,只是达到天界而已。所以对解脱的理解不同。佛教就用一个词叫做涅槃,其实就是解脱。所以印度文化本身是比较重出离、重解脱的。
印度河流域文明最早发现于哈拉帕(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境内),因而也被称为哈拉帕文化。一般认为,哈拉帕文化存在的时间为约公元前3300年—公元前1300年时期的古代文明。它是一个科学的测定,就是大概在这个期间。这个时间比我们中国的商代(约公元前1600年—约公元前1046年)还要早。这种文化被认为是印度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所创造的。现在能看到此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图章,图章上有一个人或者神在打坐,腿是盘起来的。就是说,在印度很早的时候,就有禅坐的传统,就有求解脱的传统。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。现在去印度会发现,当代印度的宗教仍然很发达。我去过印度两次,我在斯里兰卡学习过较长一段时间,斯里兰卡也有印度教的寺院。印度、斯里兰卡的文化都是很重视宗教、很重视解脱的。
(三)集体无意识
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是有差异的。中国的儒家,一般来说,中国人不把它当成宗教,只是叫它做“儒家”,当然,国外也有把儒家称作“儒教”的。而印度一直重视宗教。讨论两者文化的不同,想说明的是什么呢?就是说,中国人生来还是比较重视世俗的,我们会被生活中的大环境所影响。印度人就不一样。当然,印度人在信仰印度教、信仰宗教的时候也会重视世俗。我在斯里兰卡看到70%—80%的民众都是佛教徒,还有印度教徒,但是他们信佛跟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的信仰层次差不多的,他们到寺院去参加活动、去布施,也希望今生能够得到好的福报,真正求解脱的人并不是特别多。但是,我们也知道,他们宗教文化是非常发达的。比如说像缅甸,现在也有很多的出家人;印度有很多印度神庙,他们都是讲解脱的。虽然说不如古代那样宗教兴盛和宗教理解深入,但是至少说我们看到它的传统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在印度、在斯里兰卡,他们有些人生来就是信教了,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信教的。信教的话,出世的成分是比较多的。虽然说他们自己的侧重点在哪里都不一定,但是至少说他们这种宗教的氛围,这种出世的氛围是比我们要强烈一些。
我在出家之前,我跟我父亲打过电话说明想出家的意图。电话中我父亲跟我说了些儒家的思想,大概的意思就像我这里引的几句话一样。儒家的经典语录他背得还是蛮多的,这令我很吃惊。我父亲虽然是语文老师,对传统经典,我觉得他未必特别熟,但是在电话中他就跟我说儒家的语句,我想他怎么背得这么多,他也不是听我说要出家后,去查资料的。他在电话中就能够跟我说一些儒家的传统思想,就说我出家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,跟我们的传统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《孝经》里面说: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始也。”就是说,你要是孝顺的话,你的身体、头发都不要舍弃,这是来自父母的,你不要剃头,这是孝的开始。比如《孟子》里说: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”虽然这种观念、这种语句我们都听过,说起来我们也都知道,并不以为然。但是我们可以举个例子,很多居士是信佛教的,他也希望别人的孩子出家,但是你说让他自己的孩子出家,他未必愿意。就是说,中国人内在是有儒家意识、儒家观念的。他学过儒家思想也好,没学过也好,他的内在,在潜意识里边,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观念,它是无意识的。这跟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。
再比如说,很多中国人希望生男孩,那跟“无后为大”还是有关系的。你说他学过儒家文化,他其实也没学过,但是他会有这种观念,这是祖祖辈辈传续下来的。这与西方人的观念不同,包括现在的日本人,他们觉得孩子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。像中国人生孩子、养孩子,都会想着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要读书,还要结婚,还要给孩子买房子……像西方,父母应该是不管这么多的,管你读完高中就差不多了,你读大学的话有的父母会支持,有的父母就让孩子自己想办法;像孩子结婚了,父母是可以管,也可以不管的。所以,中国与西方在文化观念上是有所不同。
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一个说法,叫做“集体无意识”。那我们也可以把 “民族”放进去,叫做“民族集体无意识”。就是说,一个民族里面是有文化共性的。比如说,你在中国,在汉文化圈,儒家观念是根深蒂固的。虽然有时候表现得明显,有时候表现得不明显,但是都是一种无意识的。像我父亲那样的,你说他学过多少儒家文化,其实也没有。因为他是学唯物主义的那一代的,读是读过,学是学了,但是跟古代人学儒学还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他会根深蒂固地认为,作为孩子,你还是要结婚生子更好。我们是要看到我们文化里面的优势,比如儒家讲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入世精神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儒家文化里边,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,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里边,是不重出离的,这可以说是一种“缺陷”。
(四)汉传大乘佛教不重点谈出离心
中国佛教有八大宗派,都是大乘佛教。中国某些区域一度流行毗昙,流行《俱舍》,毕竟不是很兴盛。除了密宗,汉传佛教的其它宗派重视解脱道出离是不够的,这与中国的儒道文化、中国社会比较重世俗有点关系。中国佛教跟南传佛教(斯里兰卡、泰国、缅甸的佛教)是不一样的,南传佛教就是讲解脱道,重出离心,所以南传佛教不用去谈出离心这个问题,至少不需要重点去谈这个问题。
中国汉传佛教重菩萨道。像唐代,中国佛教大谈特谈各种大乘观法——“一心三观”“一念三千”“四法界观”,讲顿悟成佛,讲解脱道的是不多的,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视。当然,古人根机好,能够修得很好,能够解脱烦恼,古代的中国佛教是不需要重点谈出离心的。汉传佛教留存到今天,我觉得我们多数人的根机是不如古人的,修行的环境也没有古人那么好,所以我们把出离心、把解脱道提出来,特别去修解脱道,讲四念处,讲有余涅槃,讲更为基础的解脱道,是有这样一些背景的。我们现在学习大乘佛教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去讲解说道、出离心。因为作为一个菩萨,你的烦恼不能解脱,也是会比较苦恼的。中国佛教讲的境界很高,如顿悟成佛,但是我们其实又很难很快地顿悟成佛,修行就有点“高不成,低不就”的感觉。
如果你能够言下大悟,能够顿悟成佛,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,大悟的同时就解脱了。大乘行者顿悟佛性名为见道,他的智慧会比声闻的初果高。他同时也会具备解脱功德,会解脱烦恼。但是多数人是很难一下子开悟的,所以在我们今天修学的时候,可以重视解脱道,可以去修出离心,可以留意一下南传的内观禅法,包括汉地《俱舍论》的修法,重视解脱道。
中国的大乘佛教是将解脱道融摄进菩萨道里边来,你不能说它不讲解脱道。比如说禅宗说,“生死事大,无常迅速”,生死这件事情是很大的,要解决生死的问题,解脱是很重要的。禅宗的顿悟,包含着解脱道。我们要看到中国大乘佛教传统的长处,也要看到在这个时代它“不足”的地方,如不那么重视解脱道,于是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,如南传佛教之解脱道。我们要看出我们本身有什么问题(如不重视出离心),我们的问题有时候是集体无意识的,并不是我们有意造成的,并不是我们学习来的,可以说其实就是前世带来的,我们集体都会有这种观念。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共业。
三、识苦而出离
“三界无安,犹如火宅。” 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之三界中,无法求得真实的安宁。我们要认识到三界是苦而出离。
(一)苦谛
苦是什么?在《清净道论》里面有一个说法是比较精细的,即“苦是逼迫义、有为义、热恼义、变易义……”三界是苦,这是真理,所以叫做苦谛。
1.八苦
佛陀总结出人生的八大痛苦——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苦。世间、有情悉皆是苦,有漏皆苦,即所谓“苦谛”。只要没有证道,这个世间、我们的身心都是有漏的,都是苦的。八苦,在我们生活中都能够碰到。生苦,比如我们在母胎里边时,母胎是很狭窄的,我们缩成一团,好像坐监牢一样,这是一种苦。老苦,年老色衰,我们无法阻挡。病,没有生病的时候,我们活蹦乱跳的,一旦生病或者重病,疼痛生不如死。死苦,生死离别;有的时候死得很惨,能够“好死”是不容易的,能够安详地走,是不容易的。“死亡”是人生的大问题,也可以理解为哲学问题。思考死亡问题,能帮助我们明白很多问题。爱别离苦,喜欢的东西、人,离开我们了。怨憎会苦,两不相容的人,偏偏又聚会在一起。常谓:“不是冤家不聚头。”求不得苦,某些东西或感情我们得不到,我们会很痛苦。五蕴炽盛苦,其中“阴”,盖覆之义,谓能盖覆真性,不令显发。“盛”,炽盛、容受等义,谓前生老病死等众苦聚集、炽盛。我们这个五蕴的身心——色受想行识,是苦的聚集,所以叫五蕴炽盛苦。五蕴炽盛苦是一个总的说法,包括前面七种苦。
2.三苦
佛教还有三苦的说法,即苦苦、坏苦、行苦。苦苦,由苦事而生苦恼。像我们的病痛,本身就是一种苦受,由此而生苦,即苦苦。坏苦,乐事消去而生苦恼。快乐的感受会变化而去,会引发我们苦恼,这就是坏苦。佛教中讲苦,最根本的、最深的是行苦。行苦,“行”是迁流之义,由一切法之迁流无常而生苦恼。一切法都是无常、变化、迁流的,所以是苦的。包括舍受,即不苦不乐的感受,这种舍受也是要灭谢的,是在行苦的范围内。
行苦,我觉得是最根本的。我们现在的心念,前念和后念其实是不一样的,一直在迁流,这就是行苦。比如,我们看这张桌子、这盏灯,在我们看来,好像是不变的,至少说我们当下觉得他们是不变的,但在佛教里面认为它是有生有灭的,是刹那生灭的,只是它生灭得很迅速,前后差不多,我们误认为是不变的。
我们可以用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胶片电影为比喻来谈。那种电影的胶片,其实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,是一幕一幕的,或者说是一帧一帧的。当把胶片连续放得比较迅速的时候,就会出现一个动作连贯起来,事情就能够发生、发展了。然后配上声音,我们会看到整个事情的发生。我们会感觉身临其境。动画片的制作也是一样,画了很多动作相近的画,当快速地连贯地播放这些画,人物的动作就连贯起来,真实起来。
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事情的发生、发展,看到它是不间断的,但如果我们有定力就能看到色法其实是一片一片的,它在很迅速地变化。比如我把手从上往下放,我们看到的是一只手从上往下放。当我们把手的动作放慢下来,分解开来,会看到它本来应该是一步一步地从上往下落。所以色法是一直在变的,我们的心法也是一样,一直在变。
比如我说“念佛是谁”的时候,你分别听到的应该是“念”“佛”“是”“谁”。如果不是那么准确地说,你听到的字,可以叫它做色法,至少有四个色法。你去认知的时候,你的心其实至少是有四次认知的。所以我们的心也是在变化的。所以我们的心和色身,包括其他的法都是在变化的,这就是行苦。包括色界、无色界,其实都是有行苦的。色界虽然说有一些乐受,也是要变坏的,所以说“三界无安,犹如火宅”,都是生灭变化的。
3.三恶道之苦
佛教还有一种苦,就是讲三恶道之苦。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称作三恶道。在畜生道里,动物是比较愚痴的,可能还会被其他动物吃掉。有的饿鬼咽喉针尖般细小,口如火炬,肚子宽大无比,就算得到饮食,也没办法吃。佛教中说到很多种地狱,其中的烧炙大地狱的如此:狱卒把罪人们放置在铁城中,烈火烧城,内外俱赤,烧炙罪人皮肉燋烂,苦痛辛酸,万毒并至。
4. 人生、世界的真相和本质是苦
我们的身心和世界的构成有五种成分,即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等五蕴。《杂阿含经》卷2载:“佛告比丘:‘善哉!善哉!色是无常、变易之法,厌、离欲、灭、寂、没。如是色从本以来,一切无常、苦、变易法。……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’”色法都是无常的。无常,没有办法掌控,无常就是苦的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也是同样变化的,是苦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人生、世界的真相或者说本质就是苦,虽然说有乐,快乐的感受、事情,但这些终究要灭谢的。佛教的教法可以理解为苦的哲学。
5.苦的根源是欲贪
佛教中讲,苦的根源是贪欲。《杂阿含经》说苦的因是欲为根本。如《杂阿含经》卷32说:“众生种种苦生,彼一切皆以欲为本,欲生、欲习、欲起、欲因、欲缘而生众苦。”欲,指想要行动的意图、志趣、欲求去做。或者,也可以说苦的根源是爱欲、贪欲。《杂阿含经》卷32说:“若诸众生所有苦生,一切皆以爱欲为本。”《妙法莲华经》卷2云:“诸苦所因,贪欲为本。” 当我们没贪欲了,没有贪欲的束缚了,无欲无求,自然能离苦得乐。
(二)人生经历与识苦
南宋的辛弃疾有一首词《丑奴儿·书博山道中壁》,是在去博山路上的石壁上写的,即: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爱上层楼,爱上层楼,为赋新词强说愁。而今识尽愁滋味,欲说还休,欲说还休,却道天凉好个秋。”他年轻的时候,因为要写诗词,写一些愁忧的内容,会让人觉得他的诗词有感情,比较深奥,写得好。他为了写词,去强调忧愁。年轻时,他其实并不愁,但是现在他年纪大了,碰到很多不顺畅的事情,现在太愁了!想说都说不出来,只能说,天气太凉了,这么好一个秋天。所以人生的经历不一样,对苦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。像我是没经历太多的苦,当然我会有我的方式去认识苦,理解佛教苦的哲学。有的人他有病痛了,或者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了,或者说得癌症了,这时候他会想到来学佛。人生经历不一样,对苦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。
西方哲人黑格尔说,同一句格言,在一个饱经风霜、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,和在一个天真可爱、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, 含义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,我说,人生是苦,我现在40岁出头,我是没经历过太多的苦,我说人生是苦,你们不会有太多的感觉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在地震后的废墟里面爬出的人,说人生是苦,他是真的认识到人生是苦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,对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一般来说,经历苦难不是好事,但换一个角度来看,经历苦难却能帮助我们学习佛法,认识人生之苦痛而出离。
我们都经历过新冠疫情,2023年春节前后,大家差不多都感染了新冠病毒。在我们感染新冠病毒之前,我们是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够挺得过去的。因为我们看到报道说,有位十几岁的学生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走掉了。虽然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,感染新冠病毒其实也没什么,就是一重感冒。但是我们没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前,还是人心惶惶的,医院没有床位,药品买不到。我们也听到说在火葬场排队排得很长。所以,新冠疫情之后,我会对自己的人生安排多一些思考,我觉得每个人也都会有一些思考吧。现在有一些研究,会去研究新冠疫情对我们人类社会到底有多少影响,在疫情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改变。我自己的变化是什么呢?我会觉得时间就是这么多,我会用这些时间去做我觉得重要的事情;有些事情我觉得不重要的,我就不会去做的。比如,我在斯里兰卡读书、教书,也有八九年了。我在斯里兰卡教书的课时是很多的,一周就有十几个小时。今年,斯里兰卡的课我就没有去讲,网络课我也没有上。 所以,我觉得人生经历不一样,对苦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,对苦认识越深刻,你后面的时间越好安排,你会希望把时间用来修行,这是跟人生经历相关的。
(三)思惟苦而出离
思惟八苦、三苦、三恶道之苦,而后发起出离心,使我们精进地学佛求解脱。这是通过思惟苦而出离。《增一阿含经》卷26载:“戒成就比丘当思惟五盛阴无常、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;亦当思惟苦。”《菩提道次第论》对这个方法做了详细地整理。“思惟苦而出离”是比较容易能够用起来的方法。
四、思维暇满人身而修行出离
凡夫心与无明、烦恼相应,喜欢追求欲望的满足,即使我们知道无常的道理,也不想着出离,不是住于常见中,就是住在断见中。无明,即愚痴,不了达事、理。我们被无明所罩住,无明像一张看不见的网一样罩住我们,使我们处于迷暗的状态,不能够真正认识无常和苦,不愿意出离,活在我们固有的世界里。通过思惟暇满人身可以帮助我们出离。我们能够得到人身是很难的,我们能得到人身而又能够值遇佛法就更难了。经里说:“得人生者如爪上泥,失人生者如大地土。”就是说,我们今生的能得到人身是不容易的,就像我们手上的泥土一样,一点点,几率是很低的;但是我们来生得不到人身,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,就像大地的泥土一样多。《杂阿含经》中有“盲龟值浮木”的比喻来说明能够生而为人是很难的。这比喻是如此:大海中有一只老盲龟,寿命无量劫,每隔一百年,会浮起来探出头来一会儿。在这汪洋的海面上,有一块有一个小孔的木头,在大海中漂浮不定,一会儿东,一会儿西,随波逐流。这只龟百年一次浮出水面,能刚好把头伸进木孔的几率是极小的。如果我们失去人身,想再一次得到人身,比这只盲龟的头值伸到木头小孔还要难上很多。
远离八种无暇,具足十种圆满,满足这十八种条件,才能叫做“暇满”人身。八种无暇分别是生在地狱、饿鬼、畜生和长寿天中,和执邪见、聋哑、蔑悷车、无佛出世。落到地狱,或为饿鬼,痛苦不堪,无暇顾及佛法。落在畜生道,会比较愚痴,很难修学佛法。长寿天,无想天和无色天都算是长寿天,恒处定中,也就不会思维佛法。人身苦乐参半,反而便于修行。即使生为人,但是执邪见,执没有前世、后世、业果、三宝等邪见也会不愿意修习佛法。聋哑,即痴呆盲聋喑哑,没有能力学习佛法。蔑悷车,即边地,没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等四众游行说法的地方,没有因缘听闻佛法。无佛出世,就没有佛法。
十圆满,即五种自身五圆满和五种他圆满。《瑜伽师地论》卷21云:“云何自圆满?谓善得人身、生于圣处、诸根无缺、胜处净信、离诸业障。”善得人身,即若得男身,男根成就;或得女身,具足女根。不是黄门等。生于圣处,即生于中国(五印度或中印度),乃至有佛四众弟子游行之区域,就是出生在有佛教的地方。诸根无缺,即六根俱全,不是残疾人。胜处净信,即净信律藏(包摄三藏)是世出世一切善法所生处。离诸业障,即不自作或教他作无间罪。如果犯了某一条无间罪,今生就不能得到圣道。我们自身具备这些良好的条件,我们才能有因缘学习好佛法。
《瑜伽师地论》卷21云:“云何他圆满?谓诸佛出世、说正法教、法教久住、法住随转、他所哀愍。”从外部的环境来说,我们具备了五个条件,即五种他圆满,才能有因缘学好佛法。诸佛出世,即有菩萨经三大阿僧祗刧积集资粮,现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说正法教,即诸佛世尊、圣弟子、一切正士为他宣说正法。法教久住,即佛陀在世和佛陀涅盘后不久,正法没有消失。法住随转,即证得正法的修行者见到其他有能力证得正法的众生,使他同样也证得正法,使他随顺教法而转。他所哀愍,即施主对修行者起哀愍心,惠施资具,如法衣服、饮食、医药等。
谈到“暇满”,是说,生而为人是很难的,能够碰到佛法是很难的,能够碰到正法那就更难了。你的身心还得没有障碍,能够听得进佛法,能够有信心,能够依教奉行,这个福报其实是很大的。我们也可以想想,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人信佛?其实并不多。有多少人能够正信佛法?好像也不多。有多少人能够正信大乘佛教?似乎也不多。信之后能够依法修行的人到底有多少?其实并不多。我们放眼全世界,虽然好像佛教徒很多,但是正信的并不多,依教奉行的其实也并不多,大概都能够数得过来的。所以我们能够信佛,能够正信,能够依教奉行,能够有因缘碰到正法并依之修行,其实是很难得、很稀有的,肯定是在诸佛前种过无量无边的善根的。我们应妄自菲薄。我们确实信佛,也有在修,但是我们也会有烦恼,好像也修不上去,但我们不应该有退却之心。其实我们是非常有善根的,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跟佛法、跟正法有很深的因缘,是很难得的。
五、念死而出离
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载:“佛问沙门:‘人命在几间?’对曰:‘数日间!’佛言:‘子未知道!’复问一沙门:‘人命在几间?”对曰:‘饭食间!’佛言:‘子未知道!’复问一沙门:‘人命在几间?’对曰:‘呼吸间!’佛言:‘善哉,子知道矣!’”佛陀的弟子说人的寿命有数天这么短的时间,佛陀说你不知道。有的弟子说人的寿命有吃顿饭这么短的时间,佛陀还是说你不知道。其实,人命在呼吸之间。你会说我还能活20年、30年,但是有时候一口气上不来,人就没了,确实人命就在呼吸之间。生命这么无常,我们可以多念佛求生净土,解决生死问题,净土法门是一个很好的法门。不管修什么法门,在当下我们要去立一个归向,念佛也好,参禅也好,你至少要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要找到解决生死问题的办法。有时候我们会说现在平均寿命有80岁左右,但是60岁走的人有,40多岁走的人也有,我身边也会有一些走的比较早的,虽然不多。其实很难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,这个的确是很难说的。所以中国佛教的功课本里边,有这个偈颂——《普贤菩萨警众偈》,晚殿结尾时都会念,这个偈颂非常好。“如河驶流,往而不返,人命如是,逝者不还。”人的生命像河水一样去了,就不会返回来了。“是日已过,命亦随减,如少水鱼,斯有何乐!”一天天地过去了,我们的寿命在减少,就像搁浅的鱼,慢慢地水少了,鱼就要死掉了,有什么快乐呢?所以“当勤精进,如救头燃,但念无常,慎勿放逸!”就像头上着火一样,我们要赶快去救火,尽快修行。后面两句是出自《法句经》。我们念念在兹,也会让我们更精进地修行。
《清净道论》对“死随念”这个法门,整理得非常详细。《清净道论》说:“欲修念死的人,独居静处,当起‘死将来临’,‘命根将断’,或‘死,死’的如理作意。”它是“十随念”之一,也是上座部四护卫禅之一。我们可以修一修这个法门。虽然它是用来修定的,但是也会帮助我们生起出离心。《清净道论》说:“勤修念死的比库,是常不放逸的。”
六、观察无常、苦而出离
我们现在修出离心可能用“思惟修”比较多,比如念死无常、念三道苦。我们学《菩提道次第论》,里面思惟修的修法是比较多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还能做一些内观——直接的观察,会更能帮助我们成就出离心。《杂阿含经》卷一说:“色无常,无常即苦,苦即非我。”观察无常,因为无常,所以没有我,没有主宰;因为无常,一切法都是不能够永住的,快乐也是会消逝的,所以它是苦的。世间是没有乐的,哪怕说是乐的也是无常的。我们这个世界、人的身心都是无常的,是一种行苦。做一些内观,就能直接观察到我们身心是苦的。比如你可以看你的心念,我们心念现在就是在无常迅速地变化,念头就像流水一样快速流转。能直接观察到心念是无常的,会有更强烈的出离心。如果我们的心是无常的,我们心念的对象——境界也好,色法也好,也是无常的。《清净道论》中将观智分为十六种,其中的怖畏现起智是观察诸行的生灭而生起的,进而生起过患随观智、厌离随观智、欲解脱智等,成就这些智慧都是在帮助成就出离心。所以内观——直接观察,是非常重要的。
七、识涅槃而出离
认识到涅槃而出离。无常,我们都知道。中国传统文化经典《周易》中的“易”,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变易,也就是无常。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运动变化的,唯物主义者也知道无常。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是无常的,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想求解脱。我们可以苦中作乐,至少是有些乐受,一些快乐的事情当然也会有。但是我们要知道,你认识的苦是一方面,还要认识到有涅槃,这是另一方面。你觉得真的有涅槃,你才会真正出离,你才会愿意出离。当我们看到行苦的时候,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生、世界的意义并不是特别大,它是无常迅速的,只有涅槃才是乐的,才能够完全离苦的。
什么是涅槃?有时候可能讲得很复杂,但是说简单也简单,我们可能对这个概念理解得不是特别透彻。涅槃一词的梵文是nirvāṇa。因为涅槃一词是梵文语词音译过来的,我们理解的时候会隔着一层,理解的时候可能会有障碍。涅槃即灭却烦恼之状态。其实就是你的烦恼没有了,就是涅槃。到底有没有个地方叫涅槃,这个并不重要。经文里说,你的烦恼没有了,就是涅槃。对于涅槃,说一切有部和经部对涅槃的理解也是有不同的,大乘佛教还讲无住处涅槃。不需要把涅槃想那么复杂,把“烦恼没有了”理解为涅槃就可以。这不是我说的,是《阿含经》里面说的。如《杂阿含经》卷18记载:“涅盘者,贪欲永尽,瞋恚永尽,愚痴永尽,一切诸烦恼永尽,是名涅盘。”没有烦恼就是涅盘,我们现在有烦恼就不是涅盘,当烦恼灭掉了就是涅盘。
我们的人生是在三世两重因果里边。我们前世因为有无明、行两支,即过去世的惑业,为招感现在世识、名色、六处、触、受五支的因,识等五支是现在世的果,这是一重因果。爱、取、有三支是现在世的因,爱、取是烦恼,有是业,现在世的惑业,为招感未来世苦果的因。未来世的老、死二支是现在世惑业之因所招感的果。这是第二重因果。有前世因就有今世果,有今世因就有来世的果。我们经过修行,把无明去掉了,把爱、取去掉了,那就没有来生的生和老死了。当我们没有烦恼的时候,那就没有来生,就不会在三界里边轮转,就能够解脱,得到涅槃。所以说涅槃复杂也挺复杂,说它简单也可以是很简单的。
涅槃,可以理解为一种乐。《杂阿含经》卷41中说:“有身之欲,亦复无常、变坏之法,有行灭、涅槃、出离之乐,汝当舍离有身顾念,乐于涅槃寂灭之乐为上、为胜。”涅槃是出离之乐,寂灭之乐。涅槃乐不是感官之乐。它没有烦恼的恼乱,不用受行苦,即不用受变化之苦。它是没有苦的,那时它就是乐的。《别译杂阿含经》卷4云:“能修布施者,大获于功德,后得涅槃乐。”这里也提到最终获得涅槃乐。
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文化其实很难想象说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三界,儒家说要入世平天下,道家说可以羽化成仙,那么,我们干嘛要选择寂灭呢?所以,在文化上,中国儒道文化与印度文化是有差异的,当然,我们也可以去会通。会通到什么程度,还是取决于我们去理解儒、道的时候应该怎样去理解,都是有很多诠释的角度的,至少大体来看,中国儒道文化与印度文化区别还是比较大的。
八、《鞭子经》——告诉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
阿含藏里有一部名为《鞭子经》的经典,此经所讲的道理对我们发出离心非常有意义。这部经有汉译本,也有南传的本子。经里说世间存在着四种贤骏马,用四种马比喻四种不同根器的人。
经中说,当驯马师一扬起鞭子,马看到鞭子的影子,便知道主人的心意,就会惊怖、畏惧,立即放足奔跑。这种马非常聪慧,能够明察秋毫,是第一种贤骏马。
第二种马,当驯马师用鞭子打它时,马看到鞭影,却无动于衷。当鞭子打在马的皮毛上,马才惊怖,心生畏惧,便放足奔跑。
第三种马,它看到鞭影后,并不惊怖,不生畏惧;鞭入身毛了,也不惊怖、不生畏惧;当鞭子打在它的皮肤上,它感觉到疼,才惊怖、畏惧,而放足奔跑。
第四种马,它看到鞭影后,并不惊怖,不生畏惧;鞭入身毛了,也不惊怖,不生畏惧;鞭入皮肤了,也不惊怖,不生畏惧;当鞭入骨头了,才惊怖,心生畏惧,而放足奔跑。
以上这四种贤骏马聪慧程度是不一样的。这四种马好比四种根器不同的、聪慧程度不同的众生。
第一种贤良人,他听闻隔壁的村子有人受苦或死了,他因此惊怖、心生畏惧而出离,如理勤奋,自我努力,最终证果。这种人非常聪慧。此种人类似于第一种良马。
第二种贤良人,听闻到隔壁的村子有人受苦或死了,不会因此惊怖、心生畏惧,而是亲眼看到隔壁的村子有人受苦或死了,才会惊怖,感到畏惧,想要出离,进而证道。此种人类似于第二种良马。
第三种贤良人,听闻隔壁的村子有人受苦或死了,亲自看到隔壁的村子有人受苦或死了,不会因此怖畏,但他亲眼看到他的亲族或血亲受苦或死了,因此惊怖、感到畏惧,发心出离,而成就道业。此种人如同第三种良马。
第四种贤良人,听闻隔壁的村子有人受苦或死了,或亲自看到隔壁的村子有人受苦或死了,乃至他亲眼看到他的亲族或血亲受苦或死了,都不会因此惊怖、感到畏惧,但他自己身体感受到激烈的、猛烈的、强烈的、不愉快的、不合意的、夺命的苦,他亲自遭遇到了苦,才会惊怖,感到畏惧,发心出离修行,成就果位。此种人如同第四种良马。
这四种贤良人的根器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可能不像前两种贤良的人那样有慧根,知道尽早出离。若能像第三、四种贤良人知道出离,也算是很有慧根的。出家前并没有受过太多的苦,就是读了这部经,我才想到要赶紧出离,接着出家学佛。
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感受不到太多的苦,但是通过佛法我们确实认识到世间、人生的本质是苦的,而且有涅槃的存在。当我们知道这些道理后,应该马上求出离、求解脱。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的抉择,像《鞭子经》里第一种贤良的人一样,听闻隔壁的村子有人受苦或死了就知道出离。我们应该做一位有智慧的人。我们没必要等到生病生得很重的时候才想到佛法,等到自己快要死的时候才想到佛法。我们可以思惟苦,特别是做一些禅修,直接去观察无常,我觉得更能够触动我们,更能够刺激我们精进修行,进而能够离苦得乐,进入涅槃。
这次讲座只就解脱道讲解脱道,没有把解脱道放在大乘菩萨道里边来谈。